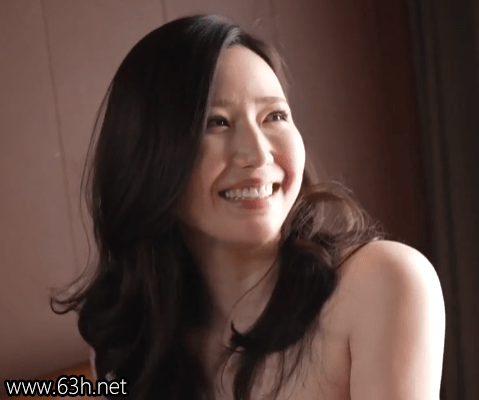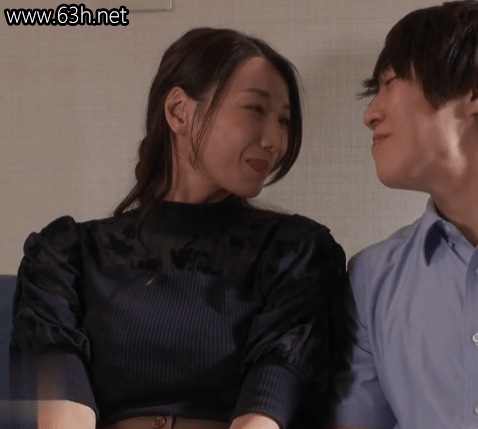花守夏步(Hanamori Kaho,花守夏歩)第一次踏入那片被称作“乌鸦谷”的地方时,天色已经压得很低了,乌云像是被人用墨泼过,沉重得几乎能把空气压碎。她提着一个小小的布包,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物和一本母亲留下的旧笔记本,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。风从山口刮下来,带着湿冷的气息,掠过她的脸,仿佛一只冰冷的手在提醒她,这十天不会轻松。她深吸一口气,指尖攥得发白,还是硬着头皮走进了魔女城堡的大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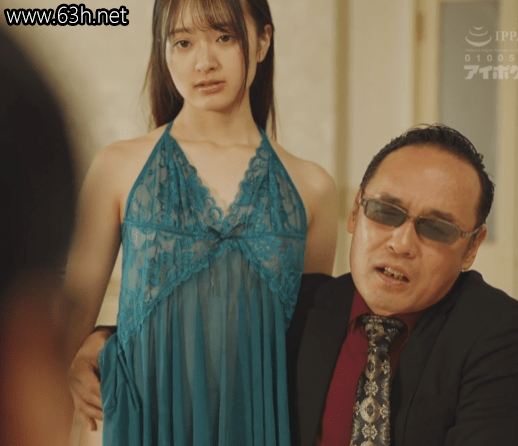
说是城堡,其实更像是某种活着的生物。那高耸入云的尖塔仿佛直刺灰色的天幕,黑色石墙上长满了奇怪的藤蔓,藤叶在风中轻轻摆动,仿佛在无声地注视着每一个来者。花守夏步跨过门槛时,地面轻微震动了一下,仿佛城堡对她的到来表示某种欢迎,又像是在衡量她的价值。她知道,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母亲的病情拖不起,而那颗仙丹,是唯一的希望。
魔女名叫瑟琳,长着一双几乎透明的灰蓝色眼睛,像冰湖一样没有温度。她高坐在一张镶满宝石的骨质王座上,手指轻轻敲着扶手,仿佛在算计花守夏步未来的每一口呼吸。瑟琳没有说废话,只丢给她一张羊皮卷,上面写着十天的“工作清单”。花守夏步一眼扫过去,心口立刻凉了半截。第一天,她要打扫“回声长廊”,一条长达三千步的走廊,地面铺着会流血的黑曜石砖。第二天,她要给“沉眠之井”换水,井水里养着能咬人的水影蛇。第三天开始,每一天的工作都比前一天更加危险,简直像一场有去无回的考验。

第一天的回声长廊让她差点崩溃。那是一条长得看不见尽头的走廊,两边挂满了古老的镜子,镜面模糊,仿佛覆盖着一层灰雾。但当她用抹布擦拭时,镜子里突然浮现出无数陌生的面孔,有男人,有女人,有孩子,眼神或愤怒或哀求,嘴唇一张一合,仿佛在对她说话,却没有声音。直到她退后一步,才发现那些嘴型都在说同一个词:“逃”。花守夏步慌得抹了一把脸,不敢再看镜子,只低着头拼命擦地。可是走到走廊尽头时,一面巨大的铜镜挡住了她的去路,镜中映出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,却比她更瘦更憔悴,眼睛布满血丝。那“另一个花守夏步”开口说:“你以为十天后你还能走出去吗?”
第二天更糟。沉眠之井藏在地下深处,花守夏步一路提着油灯走下石阶,潮湿的空气让她呼吸困难。井口周围镶着奇怪的符文,每隔几秒就会闪出一丝蓝光。瑟琳交给她一只青铜水罐,让她把旧井水倒掉,再用井底的“初源之泉”重新注满。但井水漆黑如墨,一点灯光也照不进去。她小心地用水罐舀水,忽然感觉井底有什么东西在移动,紧接着一条半透明的水影蛇猛地扑出,獠牙在油灯下闪着寒光。花守夏步本能地后退,脚下一滑,差点跌进井中,千钧一发之际抓住了井沿。她的心跳快得像要冲破胸腔,那一刻,她明白了瑟琳根本不是在让她干活,而是在用任务筛选猎物。
到了第三天,她才发现魔女的城堡并不仅仅是建筑,而是一种巨大的、活着的生物。夜里她睡不着,躺在小小的佣人房里,听到墙体深处传来低沉的心跳声,一下一下,仿佛整座城堡在呼吸。她起身推开窗户,看到远处悬空的花园里漂浮着一轮黑月,花园里的花全是灰白色的,花瓣微微发光,却没有一点香气。她还看到一群无脸的仆人,穿着破旧的长袍,在花园中无声走动,动作整齐得像被操控的木偶。她心里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,觉得这十天不仅仅是还债那么简单。
第四天到第六天,她的任务越来越离谱。她被派去“失言书库”抄写古籍,那些书会在她写字时低声念出各种诅咒;她还被要求去“灰烬温室”采摘一种名叫“幽梦果”的果实,果子甜得发腻,可一旦闻到香气太久,就会陷入永远的梦境。她亲眼看到一个和她同来的佣人忍不住多闻了一口,当场倒地,呼吸停止,身体在几分钟内变成了一团灰烬,被温室里的藤蔓轻轻卷走。那一幕让花守夏步胃里翻江倒海,却又不得不强撑着继续采摘。
第七天夜里,她终于见到了魔女最隐秘的“收藏”。瑟琳召她到尖塔最高层,那是一间由水晶构成的圆形房间,墙壁像冰一样透明,里面漂浮着一百零八个“灵魂灯”。每盏灯里封着一个小小的光点,微微闪烁,像是在呼吸。瑟琳用指尖点燃其中一盏,火焰跳动间,花守夏步看到光点变成一个女人的影像,那个女人和瑟琳极其相似。魔女轻声说:“她们是我过去的自己。”花守夏步听不懂,但瑟琳笑了笑:“你想要仙丹?等十天过后,你也会在这里点亮一盏灯。”
第八天,城堡开始对她做出反应。她走过回声长廊时,镜子不再显示陌生的面孔,而是开始映出母亲的身影。母亲在镜中微笑着对她说:“别怕,回来吧。”花守夏步差点伸手去触碰,幸好最后一刻停住了。她越来越清楚,城堡里的一切都在试图侵蚀她的意志,只要稍有动摇,就会被彻底吞噬。
第九天,风暴降临。整座城堡开始震动,尖塔上的符文闪烁得像一千只眼睛在睁开,仿佛有什么被封印的存在正在苏醒。瑟琳的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,她让花守夏步在中央大厅画下保护阵,并把一枚黑色戒指塞进她手心:“如果我没能回来,就戴上它。”那一夜,花守夏步第一次看到瑟琳全力施法,数以百计的魔法符号在空中翻涌,化作一条由雷光组成的巨蛇,和从虚空中伸出的黑手纠缠撕咬。她几乎被震得耳膜破裂,浑身被光影包裹,直到彻底失去知觉。
第十天清晨,她在佣人房醒来,一切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城堡恢复了平静,瑟琳坐在王座上,淡淡看着她:“债清了,走吧。”花守夏步握紧母亲的仙丹,转身离开,却在大门外停下了脚步。她回头望去,远处的高塔在晨雾中若隐若现,仿佛一场荒诞的梦。然而,她心底清楚,那十天的每一刻都是真实的。她甚至感觉,自己的影子比离开时更长了一些,仿佛有一部分灵魂还留在城堡里。
可她没注意到的是,当她走出乌鸦谷的时候,指尖那枚黑色戒指,微微亮了一下。
花守夏步离开乌鸦谷的时候,天边刚刚透出一丝曙光,山雾像一条缓缓游动的白蛇,缠绕在城堡和林间。她一步一步走下山路,脚下是湿滑的青石板,每一声脚步都像敲在心口。她告诉自己,一切都结束了,母亲会好起来,生活也会回到正轨。可不知为什么,胸口那种压抑感始终没能散去,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她的喉咙。她以为这是十日劳累后的错觉,直到她在林中小憩时,发现了一件让她彻底心寒的事。
她低头看见自己的影子。那影子比她高出整整一尺,形状也略显扭曲,仿佛并不完全属于她。她退了一步,影子却没有跟着动,而是微微抬起了头,仿佛在看她。那一瞬间,花守夏步背脊发凉,几乎想立刻逃跑。但影子很快恢复正常,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她不敢再多想,只能继续往家赶。可越往前走,奇怪的事情越多:鸟雀的叫声变得断断续续,溪水在她经过时泛起奇怪的涟漪,甚至风吹过树叶时,会拼凑出一些模糊的词语,仿佛在低声呼唤她的名字。
回到家后,母亲服下仙丹,病情果然迅速好转,整个人的脸色红润了许多。家里终于恢复了久违的笑声,邻居们也纷纷过来祝贺。花守夏步本该松一口气,可她却发现夜里越来越难入眠。每当闭上眼睛,总会梦见魔女的城堡,那些回声长廊、沉眠之井、失言书库和幽梦果温室一一浮现,甚至她还能清晰地听见瑟琳的声音在耳边低语:“十天结束了吗?你真的确定吗?”
她试图用各种方法让自己不去想这件事,白天帮母亲做家务,晚上点上安神的香,甚至请了镇上的老巫婆画护身符。可一切都没有用。到了第七个夜晚,她终于忍不住起身,披上外衣,悄悄走到院子里。月光下,她的影子再次异样地拉长,长到几乎触碰到院墙。就在那一刻,影子开口了。
“回去。”
那声音冰冷,带着某种不容置疑的力量。花守夏步整个人僵在原地,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线牵住。她想大声呼救,可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发不出声音。影子继续说:“你以为拿到仙丹,就真的自由了?那枚戒指,是钥匙,不是报酬。”花守夏步猛然低头,发现自己左手无名指上的黑色戒指,正散发出淡淡的红光,就像心脏在脉动。
从那一刻开始,她意识到,这十天的代价并没有结束。瑟琳不仅要她的劳力,更想让她成为某种“继承者”。而她在城堡里做的那些任务,其实是在一步步接触某个庞大的魔法契约。换句话说,她已经是魔女的一部分。
第二天清晨,花守夏步带着戒指去找那位老巫婆。巫婆看了一眼,脸色瞬间煞白,手中的木杖差点掉在地上。她拉着花守夏步到屋内,把门窗关得死死的,声音颤抖地说:“这是‘缄魂戒’,你戴上它的那一刻,你的灵魂就已经被刻下了印记。只要瑟琳想,你会在任何时间,任何地点,回到她的身边。”
花守夏步整个人愣住了,感觉血液瞬间凉透。可更可怕的是,巫婆接下来的话。
“而且,这枚戒指会在第十个满月的夜晚苏醒。到时候,你不是你了。”
花守夏步本想立刻把戒指摘下来,可无论怎么用力,它像长在她手上似的,皮肤甚至在戒指边缘微微发红,仿佛和血肉完全融合。她忽然想起第九天的风暴,瑟琳递给她戒指时说的那句模糊不清的话:“如果我没能回来,就戴上它。”可问题是——瑟琳明明活得好好的,为什么还要让她戴上?
日子一天天过去,花守夏步渐渐察觉到周围的一切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。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好,好得甚至不像是正常的康复。她的眼睛时常会闪过一丝灰蓝色的光芒,和瑟琳一模一样。而每到夜晚,母亲说梦话的次数越来越多,内容模糊,但总是反复念着“回声长廊”、“失言书库”这些花守夏步极力想忘掉的名字。
直到有一晚,花守夏步被一阵巨响惊醒,推开窗户一看,远处的乌鸦谷上空再次闪起了雷光,仿佛整个世界在呼唤她回去。戒指彻底发亮,光芒映得院墙上的影子像一扇缓缓开启的大门。
花守夏步(Hanamori Kaho,花守夏歩)这才意识到,那十天只是序章,真正的故事,才刚刚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