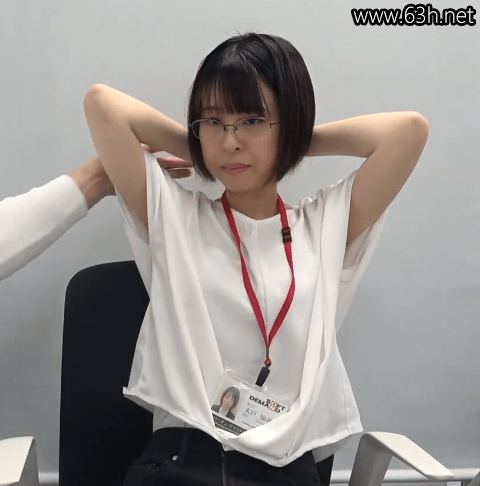那天电影院的人不多,我和朋友挑了个靠后的座位坐下,开场没多久就被带进了一个有点熟悉却又不安的家庭故事里。番号HMN-126这部片子,老实说,它不像那些大成本制作那样用光影特效吸引人眼球,但却有种让人沉进去的真实感。尤其是那个女孩——工藤拉拉,她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“别人家的孩子”,她甚至可以说是有点“难搞”。可是也正是因为她太真实了,才让人更难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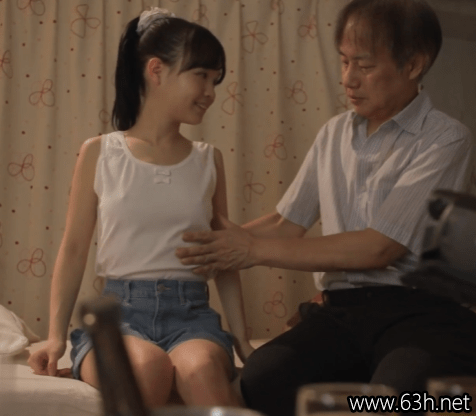
一开始的时候,工藤拉拉(Kudou Rara,工藤ララ)的眼神就是带刺的。那种防备、抗拒、不信任,混杂在一个只有十四岁的小姑娘脸上,看着真让人心里发紧。她妈妈再婚的那天,她穿着黑色的连衣裙,表情死板得像是去参加葬礼。继父是一位中学老师,看起来文质彬彬,戴着副老式金边眼镜,说话慢条斯理,可也不是软弱的人。电影没有用什么夸张的方式去描写这段新组建的家庭关系,而是一点点剥开日常生活的皮,露出那些带刺的骨头。
工藤拉拉不愿意叫继父爸爸。她用一种近乎挑衅的方式测试这个新男人的底线。晚上回家故意很晚,书包一扔就躲进房间,连个招呼都没有;吃饭时故意夹他碗里的菜,还装出嫌弃的样子放回去。说实话,看得我都有点替那男的憋屈。可继父就像是那种被打磨过无数次的石头,冷冷地、不动声色地接招。有一次工藤拉拉旷课被学校打电话通知,他没有发火,只是坐在饭桌前,轻声问她:“是不是不喜欢这所学校?”那一瞬间,她抬起头,眼里竟然有一点点惊讶。

妈妈夹在中间,是那种典型的温和型母亲,不想女儿受委屈,也怕丈夫被误解。可家庭教育不是做和事佬就能解决的事。戏剧性在于,继父不单是个老师,他还是个擅长“观察”的老师。他发现工藤拉拉虽然嘴硬,但在写作文时却流露出超出年龄的敏锐。他偷偷看过她房间里写满涂鸦的日记本,字迹乱得像打仗,但每一篇都像是在跟世界吵架。他没说破,而是开始用一种类似“攻心战”的方式接近她。
比如那次学校组织写生活动,工藤拉拉死活不肯参加,他就对她说:“你害怕自己画得不好,是不是?”她咬牙瞪着他,那眼神像要把他杀了。可第二天,她还是带上画板去了。再后来,他给她推荐了一本叫《夜晚的孩子》的小说,说这本书的女主角和她很像。工藤拉拉嘴上不屑,可回家后却偷偷看了一夜。渐渐地,镜头里的女孩开始有些变化,她还是顶嘴,但不再是为了反抗而反抗。有一次她成绩退步了,他没有责备她,而是跟她一起坐在饭厅,陪她分析试卷。他说:“你不是不行,只是不愿意相信你可以。”那句话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她心里的一扇门。
但这部片子最打动我的是它没有让一切顺理成章地“圆满”。中间工藤拉拉还是做了不少“幺蛾子”,比如她为了反抗继父安排的学习计划,跟班上一个不太正经的男孩混在一起,还偷偷跑出去夜不归宿。继父找到她的时候,她正靠在便利店门口,眼神空洞,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她像一个被世界遗弃的孩子。他没有骂她,只是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她身上,说:“下次不要这么冷的时候一个人出来。”那句话简单得让人想哭。
从那以后,工藤拉拉才算真正开始接受这个家。她慢慢地开始学习,甚至在家里设了一个小角落,贴满了早稻田大学的照片和激励语。她的目标开始清晰,她的眼神也变得有光。过程当然不轻松,她是那种不服输但也容易放弃的人。一次模考成绩惨不忍睹,她把卷子撕碎扔进了垃圾桶,继父看见后什么都没说,第二天却把一套新的模拟题放在她书桌上,上面写着:“有本事,再来一遍。”她气得牙痒痒,但最后还是咬牙写完了。
她和继父的关系就是这样,一点点地从火药味变成了温吞的温情。不是那种电视里大张旗鼓的感人场面,而是那种一碗热汤、一杯放在桌角的温牛奶、一句“早点睡”的叮咛。高三那年,工藤拉拉变得安静又执着。她开始每天六点起床晨读,连妈妈都惊讶地说:“我女儿是不是被调包了?”而她只是冷哼一声:“考不上我就一辈子被你们看笑话了。”
终于到了考试放榜的那天,镜头没有刻意去拍她激动落泪的场面,只是一个电话响起,她接起听了一会儿,然后一边掉着眼泪一边说:“我上了。”继父站在门口,点点头:“嗯,我知道。”那一刻我突然觉得,这两个人之间其实早就超越了“继父女儿”的标签,他们是一种特殊的搭档,是彼此灵魂里互相拯救的一部分。
电影的结尾也很克制,没有热烈的背景音乐,没有热泪盈眶的大团圆。只是工藤拉拉一个人提着行李走进早稻田大学的校门,镜头定格在她坚定的背影上。继父和母亲站在远处,阳光落在他们脸上,他轻声说:“她是我们最难教的学生,也是最好的。”
我想,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在青春里当过那个叛逆的工藤拉拉。番号HMN-126这部电影并没有用太多华丽的技巧去讲一个家庭教育的故事,却让人从一个女孩的成长轨迹中,看见了“理解”这两个字的分量。在这个碎片化、速食化的时代,它像是一封写给父母和孩子的长信,提醒我们,有时候,爱不是包容,而是对抗中依然不放手。
看完电影我回家的路上,脑海里一直是工藤拉拉那句:“我不是不行,只是还没找到相信自己的方法。”这句话也许不是多么华丽,却像一根钉子,把我的心牢牢钉在那个电影院的座位上。你要说它是不是一部伟大的电影?可能不是。但它确实是一部会让人不知不觉地想起自己、想起家、想起那些年自己也叛逆过的电影。那种温热,是过了好几天才慢慢散去的。
其实我原以为番号HMN-126的故事会在那句“我上了”后就落下帷幕,没想到它还留了一点余韵。影片最后的几分钟像是彩蛋,又像是故意留给观众的某种提示。工藤拉拉在东京独自租了一间狭小的公寓,镜头跟着她打开行李,取出一张旧照片,照片上是她、妈妈和继父三人坐在餐桌旁,那时候她还一脸不情愿地撇着嘴。她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,最后小心翼翼地贴在了书桌旁的墙上。
那一幕其实挺简单,但让我坐在座位上有种莫名的心酸。我们总说要离开原生家庭,去独立、去成长,但很多人终其一生,都在回望那个曾让自己愤怒、挣扎又眷恋的地方。工藤拉拉变了,变得像一个真正会思考、会选择未来的人,可你知道,她骨子里那个倔强又渴望被肯定的女孩,一直还在。
还有一段让我印象特别深的,是工藤拉拉写信给继父。她在信里第一次称他为“爸爸”。那封信没有过多的煽情语句,语气甚至有点别扭:“虽然我还是不太习惯叫你爸爸,但……我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。”那种拘谨却真诚的尝试,比任何一句“我爱你”都更动人。她没说谢谢,也没说想你,只是写了一句:“你说过我是你最难教的学生,我现在觉得,你是我最不想让失望的老师。”
电影没有回信的镜头,只有继父在学校办公室里读完信后,轻轻摘下了眼镜。阳光照在他额角的白发上,他没有说话,只是默默叠好那张纸,放进了抽屉,像是把一段漫长的战役封存进了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
很多人看完番号HMN-126可能会觉得它太平淡,缺乏戏剧冲突。但也许正因为这样,它才让人觉得贴近生活。谁的成长不是在沉默中挣扎着前进?谁不是从误解、碰撞中慢慢学会了爱与原谅?工藤拉拉的故事,是无数个家庭故事的缩影,只是它被拍了出来,安静地讲给你听,不是为了告诉你怎么做才是对的,而是提醒你:教育不一定是规训,爱不一定是迎合,有些改变,需要时间,也需要那一点点被看见和等待的温柔。
走出电影院那会儿天已经黑了,我朋友突然冒出一句:“要是我当年也遇到这么一个继父,可能现在也能上早稻田了。”我笑她矫情,可心里明白,像工藤拉拉(Kudou Rara,工藤ララ)那样有人坚定陪伴成长的人,其实并不多。于是,那部叫番号HMN-126的电影,在我们心里,不知不觉就成了一封写给青春、写给父母、也写给曾经那个“不听话的自己”的信。